
本期介紹的三本文集,分別是第 169 冊《忘憂國的神行》、第 170 冊《回首西城烟雨》及第 171 冊《玻璃缸裏的金魚》,這三冊文集均出版於 2004 年,此時已是 盧師尊進入「閉關隱居」的第四年了。
從這三冊的文集綜合看來,盧師尊對自己進入第四年的閉關生涯,統括而言就只有兩件事:日日「修行」與「寫作」。強調修行是人生大事(生死大事),而寫作也只是為了奉勸大家,不要忘記修行。所以說是二事,其實也是一事,這便是 盧師尊閉關的大事因緣。
盧師尊的生命歷程,其實就是一場「演示」。生命的前25年,他按部就班的求學、成長、工作,所演示的是如你我一般,一個平凡無奇的尋常人生。26歲卻逢奇緣,得瑤池金母開天眼,知前世因果。更獲得三山九侯靈師與眾人間上師的傳道授法,繼而神算度眾、書寫靈書,以在家居士的角色,一面修行,一面經歷人間的酸甜苦辣。38歲再蒙金母啟示,移居美國,於「巴拉」閉關三年,圓滿證得無上正等正覺,及密教虹光成就。得證後,正式創立真佛宗派,進而剃度出家,樹立真佛法幢,廣弘真佛密法。因厚積薄發,短短十數年間,便受萬眾引頸膜拜,逾500萬弟子皈依學法。此時期所演示者,即無上尊貴的密教大法王 蓮生活佛。
然而,正當萬眾矚目、眾星拱月之時,盧師尊卻毅然宣告閉關隱居,這又是何演示?盧師尊言:「佛法的種子,已種在大家的心田,只等待發芽、開花、結果。這是:聞、思、修。修『第一義空』、『無所畏』、『無所有』、『無所住』、『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』。修『無上正等正覺』,這是福中的大福,善中的大善,喜中的大喜。
而後。二十多年的西雅圖歲月逝去!我即『無我』。我演示「無貪』、『無瞋』、『無痴』。演示『一切法皆空』、『一切無所有』,我即隱去!隱居閉關而去!」
而這三冊的文集,便是 盧師尊在閉關的這一段生命時刻,不同面向的「演示」。譬如第 169 冊《忘憂國的神行》,就是他如何面對病苦的演示。即使貴為法王,盧師尊仍如你我一般,須面對生老病死的因果業力。而唯一最大的不同,就是 盧師尊親自示範,即便巨大的業力現前,一個真正的行者,仍能以真實的光明力坦然面對,進而得到超越與轉化。
第 170 冊《回首西城烟雨》,更像是人生繁花落盡後的一種放下與釋然。過去的五彩人生很輝煌,但過去就是過去了,可以懷念,但必須放下。而《玻璃缸裏的金魚》,則是對現狀的接納與反思。如今離群索居,看似困居一方,實則人生過去的輝煌,又何嘗不是另一個魚缸呢?所以入世弘法和出世隱居,對 盧師尊而言,是一不是二,只是真實的演示:「一切法皆空,一切無所有。」


第 169 冊文集《忘憂國的神行》,出版於 2004 年,是 盧師尊在隱居葉子湖之時,寫下於「神遊」期間隨著感應救濟和度化眾生的事蹟。書名中「忘憂國」的意思,是指 盧師尊在隱居閉關的三年裡,不受外界打擾而以寂寂為樂,也就是「忘憂」,如書上所說:「我住忘憂國也」;而「神行」則是 盧師尊在「定」中心無罣礙的「任運」,隨感隨應的神遊諸法界,並隨緣教示佛法的真理。
盧師尊在這段閉關修行的時期,主要仍是在「斷煩惱」、「了生死」的行持。寂靜的隱居生活,使 盧師尊常處於「忘憂極樂」的修行境況,念念的「清淨」更讓他時刻與佛法言行合一,縱然書上提到的神行,只是「五神行」中的「病神行」:「四大分散,腦分八瓣,中陰元神自出自入,以『病苦』為神行」,也一樣在法界裡任運自如、光明顯露:「我已修至『有法』等於『無法』,『一切事』等於『無一切事』,這世界發生了什麼大事,我也等於無事了。在『神行』中,能救則救,不能救,完全不放心上,就算救了,也不放心上,就這樣,隨性而去吧!」
在神行過程裡 盧師尊行蹤所到的境界,例如是:血光國、心通國、五不還天,以及書上述說在法界遇上的情節發展,均有其背後的佛法深義,當中有著佛陀教示的緣起法中「因緣果報」的真理。譬如《雜阿含經》裡所云:「此甚深處,所謂緣起」。簡單來說,法界的顯現和世間事物存在的有與生起,必然是有原因的,亦是與緣起法「此有故彼有,此生故彼生」的定義一樣。這是佛陀於宇宙真理中所得出的結論,也可說是佛陀在因果相互依存關係裡的體悟。所以佛陀在經典上說:「非我所作,亦非餘人作」,因為,這本來便是因果定律的真實相。
《忘憂國的神行》一書的內容,就是要展現世間「因緣果報」絲毫不爽的玄妙處,藉文集篇章內的故事,彰顯心存善念的重要性,因為眾生在世間皆有業報隨身,正如《十善業道經》內說:「今大海中所有眾生,形色麁鄙,或大或小,皆由自心種種想念,作身、語、意諸不善業,是故隨業各自受報。汝今當應如是修學,亦令眾生了達因果,修習善業...。」
故此,盧師尊在書上一再提醒我們要遵循佛陀的教義,常要保持一念清淨,多行善事,時刻警惕自己勿造惡業。譬如在書中的<善神與惡鬼>、<兔唇的女兒>、<無法救度的事實>等章節裡,就是列舉他所親自看見「因緣果報」的應驗事蹟,而讓人們反省自身當下的思惟與行為。
書中寫出了學佛修行中「知過懺悔是正道」的道理,而在十五篇<神行的詩篇>之中,更以優美的文句敘說佛法的種種旨趣。讀者若能細心領會文句中蘊藏的要義,對於更全面了解及深入研習佛法的理趣,是極有幫助的。說不定,由此而轉化了命運、超凡入聖,終能體會到娑婆一世的真正意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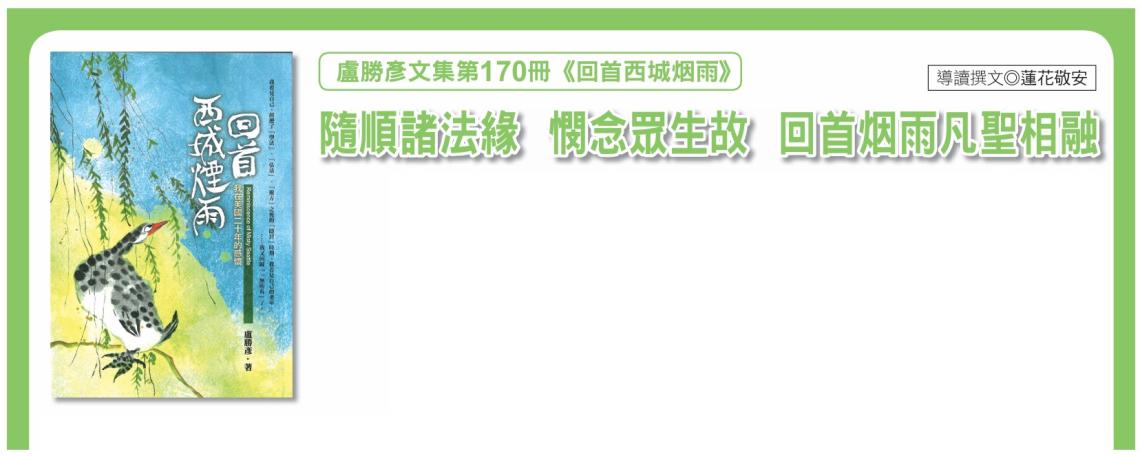
第 170 冊《回首西城烟雨》,是 盧師尊完成於 2004 年的文集,歸類在「散文詩集」的著作。內容包含著 盧師尊回首過去二十年來的移民歲月,日常生活裡的點點滴滴,和在修行心得上的無私分享與紀錄。篇章裡並有著「勝義諦」與「世俗諦」互為依附的啟蒙。因為在佛法的角度來說,我們本身就是活在「世俗」的世界裡,學佛者於修行上若沒有「世俗諦」的「名」和「相」,以及「二諦」互為對比的前提下,日後又怎能契入佛法的甚深空義之中呢?這個也正是「依不了義而入了義」的道理,譬如摘錄自《中論頌》裡所云:「若不依俗諦,不得第一義」的含意。
這本書冊是由 91 篇散文 (隨筆) 的文學體裁所集成,內容是述說盧師尊為何舉家移居美國的緣由,和在這二十多年內四次遷居的原因,以及旅居美國期間所經歷的人與事...。在這段獨自一人隱居閉關的期間,盧師尊寫出在西城渡過的那些歡樂共聚的日子,緬懷已逝去的歲月與人物思念的文章,又彷彿讓我們看到了人間「無常」的真實相,令人慨嘆青春年華的流逝匆匆。
事實上,書中告訴我們,盧師尊雖已是大成就者,但卻與我們同屬有情眾 (心、佛、眾生,三無差別),分別的只是他在佛法上是開悟者並已實修證道,並且,不會因為自己的成就而看不起眾生,展現出佛法裡「天地有情、普同尊重」的仁慈博愛精神:
「我悲切。我失落。我憂傷。就是為了廣大的眾生而悲慟!我深感世人為欲望所縛,貪瞋痴造業受報,冤冤枉枉地受六道輪迴之苦,實在太愚蠢、太悲苦。人們宜及早選擇合適的法門,勤懇實修,才能明了自性光明,而自主生死,同出苦輪,這才是人生價值的所在。」
《回首西城烟雨》一書,記載著 盧師尊在一次禪觀中,看見彌勒菩薩前來打開布袋,從虛空中飄下一頂「紅冠聖冕」戴於 盧師尊頂上的事蹟,也就是真佛經內「彌勒菩薩戴紅冠」的典故;並說出瑤池金母帶著盧師尊去看「水中倒影」,知曉自己一生命運的發展,乃至一位來自三十三天的天子,告知他未來將會遇上的境況,然而,盧師尊卻以一心弘揚佛法為要務,其他的只覺不重要了。而在這些文章情節裡面,均有著令人們省思的佛法理趣:
「天子說:『你不為己?』
我答:『我的未來已知,從死寂而開始,最終又歸於死寂,中間的燦爛,如曇花一現,我過去一無所有,未來也一無所有,我的成就是自心明白成就』。」
盧師尊在這部書上,尚有教示「入世」與「出世」的和融之道,指出真佛宗的「建寺」,不是為了世俗的名與利,只著重於繼承密教的「實修」,西城雷藏寺的特質,原是:
「有入世的方便問事,有出世的開般若慧。修密,一咒一印一本尊。修顯,老實念佛。修禪,三昧成就。修火供護摩,自入福慧寶藏...。」
本書篇章之多,全是敘述對佛法見解的精闢獨到之處,和 盧師尊以回憶中的西城往事,引導出凡聖同體的道理,令見聞者一一受益。因此,讓我們暫停下為生活忙碌的急促脚步,一起與作者回到那濛濛烟雨裡,重拾回自我的真實。


盧勝彥文集第 171 冊《玻璃缸裏的金魚》,同樣出版於 2004 年。盧師尊自 2000 年 8 月於香港首傳「時輪金剛」大法後,隨即進入閉關隱居生涯,迄今已四年。弟子們完全無從得知 盧師尊的一切近況,甚至究竟隱居何處,亦無從知曉。幸好,盧師尊仍然持續寫作不斷,仍舊維持每兩個月出版一冊文集的規律,讓弟子們還能夠透過文集,感受 盧師尊的所思所感。
一個人長久閉關,在一方小天地,不見外人,惟見己心,一切眼耳鼻舌身意的觸,都限縮到最小、最少。若非真實經歷,一般人實在難以想像此種心境。所以 盧師尊在〈玻璃缸裏的金魚(序)〉文中,如此描寫他隱居的心境:「葉子湖的隱居處如『玻璃缸』。我就是『玻璃缸裏的金魚』。昔日,五百萬弟子,如今一人而已!昔日,眾星拱月,如今凄涼孤獨!昔日,巨宅莊園,如今獨臥草蓆!昔日,乾坤到處,如今只剩一心!一心往生淨土。我這金魚在玻璃缸中,自得其樂就是『修行』與『寫作』,大家想一想:地球也是個玻璃缸,大一點的玻璃缸。再想一想,是有很多人生活在大玻璃缸中,但,你有知己嗎?可能相識滿天下,但知己無一人啊!這和我(獨居行者)豈不是一模一樣嗎?」
為什麼要隱居閉關?這樣的行為究竟有何意義?盧師尊以達摩祖師為例,他也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,是中國禪宗之始祖。盧師尊自問:「面壁九年。口不語。身不動。念頭想什麼?或是無念?或是神行?或是觀照?或是懺悔?或是虛空?或是光明?或是等待有緣人?這是很耐人尋味的問題。」
而 盧師尊自己呢?自喻為一隻隱居閉關在玻璃缸中的金魚,行、住、坐、臥、游,全在玻璃缸中…:「我在想什麼?坦白說,我是『神行』,還有我是在『懺悔』消業障,大家不要以為師尊一生很神聖,其實不要驚愕駭然。我這一生是有過貪、瞋、癡,種種意念上的壞念頭也是有的。我這隱居閉關,靜坐常思己之過。因此,我誠誠懇懇的懺悔,拜禱本尊,痛改前非,力行善事,要忍辱,要永恆行善,拜懺之後,不管如何,大小難易,不可再犯。誓除諸『妄念』,達於『無念』。」
其實,修行人閉關隱居是必要的,只是其中的因緣與時間點的抉擇,卻是因人而異。在〈命運須自己拿捏〉一文中,盧師尊以六祖惠能為例,彼時惠能大師得五祖衣缽後,為躲避追殺,隨即隱入獵人隊中,共十六年之久。經過十六年,才坐定「曹溪」道場,大弘禪門頓悟之風。盧師尊言:「六祖是先隱後弘,我是先弘後隱。我覺得『悟道』之人,命運須自己拿捏,否則也是滿危險的,六祖得法衣。(有人就不服)從此忍辱十六年。我得『天眼』,也『見性』。『聲名大噪』後,趕緊移民美國西雅圖,在『巴拉』先隱居三年。若不移民,也滿危險的。等大法傳的差不多了,我又隱居閉關去了。我說,這些都是命運使然,須自己拿捏得住。我始終記住師父的話,『譽之所至,謗亦隨之。』」
然而,不論 盧師尊所悟為何,不論出世入世,弘法或閉關,永遠都心繫眾生。即便只是一隻在玻璃缸裏的金魚,仍不忘「修行」,不放棄「寫作」。只因「修行是人生大事(生死大事),而寫作是奉勸大家也修行。所以二事是一事,大事因緣。」








